
撰稿/左瑞 “我们来中青赛干什么?不是来陪太子读书!”胡德光大喊,“我们就是要打进16强!张喆宁,你的目标就是要进国字号!”亳州体校主教练声嘶力竭的赛前动员,是这支组建仅两年的球队破茧挣扎的生动体现。

走出安徽参赛,“亳州”两字常常被误认,错叫成“毫州”。在唐山,一面旗帜展现了他们对家乡的自豪,特别标注了“亳”的正确发音“bó”。作为华佗、曹操、花木兰等历史名人的故乡,亳州体校自2019年成立以来,致力于推广华佗五禽戏和培养竞技人才。2023年启动足球项目时,由于缺乏本地专业教练,市文旅体局特地从合肥引进相关服务。
与拥有52年历史且具备办学资质的合肥体校相比,亳州体校只能开展业余训练。球队成立后,由亳州十一中提供学生学籍、场地和食宿保障,体校则负责在市内及全省范围内选拔人才,并提供专业师资和训练比赛经费。“我们体校90%的孩子是因为热爱足球才加入,剩下的则希望通过足球特长考入大学。”胡德光表示。

40岁的胡德光曾效力成都五牛,是合肥一家青训俱乐部的创始人;这批打入中青赛初中U15全国总决赛的队员,是亳州体校的首批足球运动员。此前,他们在各自学校已接受了数年训练,进入体校后脚下技术虽有提升,但在中青赛上仍显不足。
两年春秋更迭,队员们在十一中结束一天的学习后,每晚8点到9点半坚持训练。寒暑假期间学校封闭,球队就转到合肥集训。夜晚灯光下的刻苦训练,使他们在本市无往不利,在徽青赛也打破了合肥球队的垄断,但到了中青赛大区赛,“我们的技术不如人,全靠拼劲出线。”队员冯韶阳说,主教练要求他们“每场都当作最后一场来踢”。
首次晋级中青赛总决赛的亳州体校在唐山依然全力以赴。小组赛首战以1比11不敌鲁能校U14,第二轮2比1险胜重庆凤鸣山中学,第三轮0比5败给陕师大附中。每一场比赛,他们都凭借强健的体魄、顽强的意志和紧密的防守与对手较量。
在以小组第三晋级附加赛的过程中,球队付出了沉重代价:中场冯韶阳因铲球拿到第二张黄牌被停赛一场,前锋程世博在对抗中受伤被救护车送往医院。虽然附加赛对手是上届亚军清华附中,但胡德光鼓励队员:“小组第二第三没区别,我们还没被淘汰!”一天后,他们以1比10结束了总决赛征程。


赛会期间,像清华附中、恒大足校等队的比赛,总有几十位家长在场外风雨无阻地为孩子加油,赛后还会赶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嘱咐并拥抱孩子。他们会千里迢迢到比赛城市租房,“孩子去哪比赛,家长就跟到哪”。
而体校队伍比赛时,这样的温馨画面却很少见,只有几位大同体校球员的家长来到唐山。除了时间和经济成本等原因,大同体校领队孙雨还认为:“也许我们队员的家长,对孩子的期望没有其他队那么高吧。”
公立体校的吃住、训练、比赛全都免费,为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踢球的机会。亳州体校超过三成队员是留守儿童,球队为他们创造了用足球驱散孤独、避免自暴自弃、甚至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关爱缺失,队员们在学业和足球的充实生活中收获了更多温暖。胡德光不仅要负责技战术,还要操心生活琐事,有时觉得带队很辛苦,“既是父亲又是母亲。”但他也理解队员难管的原因,“他们也很不容易。”

整个赛区最忙碌的主教练,每场比赛都被动应战,时刻高声提醒队员,希望借此提升执行力。“布置好的战术怎么没有落实?只要按我的要求去做,比分绝不会这样!”队员们拼尽全力,胡德光也总结球队特点为“防守凶猛、拼抢积极”。
虽然蚌埠曾培养出李毅、韦世豪等球星,但安徽足球在中国足坛一直较为低调。近年来合肥率先推动校园足球,“振兴三大球”也在各地逐步实施。亳州体校中青赛跻身32强的成绩,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,也突破了主管部门的原有预算。为此,胡德光自掏腰包垫付参赛费用,最终在市文旅体局三级调研员、球队领队张焱的帮助下争取到了这笔资金。
但目前最大的难题不是经费,而是球队的存续问题。初中毕业的这批球员因比赛错过了亳州十八中的足球水平测试,导致该校今秋20个足球特长生名额只招满了1人。其实他们的文化成绩不错,90%能上高中,其中三成能进重点,但如果队员分散到不同学校甚至回到原籍,之前的训练成果将难以延续。“回去后我们要和教育局尽快协商,争取让球队集中到一所学校。”未来两年,U14、U13队伍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。
胡德光认为,球队能走到今天,已经是体教融合的成果,但还需继续努力。对于球员中考后的出路,他觉得主要有特长生和职业球员两条路。有的队员已被纳入国少人才库,也有人还很迷茫,“我也不知道,来体校就是想多踢几场比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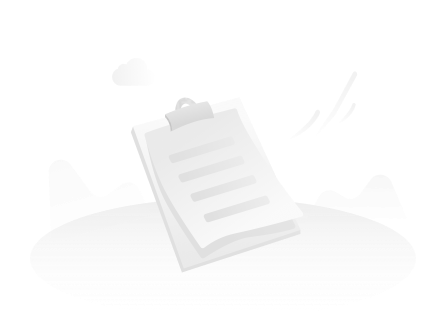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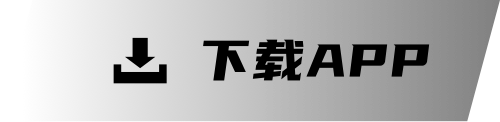




 网站地图
网站地图
 联系方式
联系方式
 应用下载
应用下载


